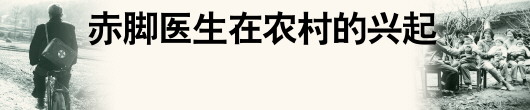|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近报 新闻 时间:2018年02月02日 来源:近报
中国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使毛泽东极为不满。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终于使他在1965年发怒。可能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发怒,使农村医疗卫生的普及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而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就这样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了,农村医疗状况得到了迅速改观。
毛泽东作出“六二六”指示 旧中国的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也治不起,只是挺着,小病能挺过去,得了大病,只能等死。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也曾采取多种具体措施去解决。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政府很难一朝一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中药,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有利。1958年他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是留在城市的医院中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于是转而探索另一个解决方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 毛泽东内心积压的火气,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爆发了。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泽东发怒后,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指示的办法。由于毛泽东这次发怒中作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卫生部把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事情。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此后,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了。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有一些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 上海首现“赤脚医生”叫法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就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原来,这个公社于1965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在学习中,她十分刻苦。后来她自己回忆道: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比方那些化学元素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由于王桂珍在班上学得认真,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之一。当时,江镇公社第一批卫生员有28个。这些卫生员,实际上仍是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农民生病,还是要到公社卫生院来。换句话说:公社培养的卫生员还是没有像过去乡村游医那样走村串户到农民中去给农民治病。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农民们并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只学了4个月就能当医生?能看病吗?但王桂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一个病人牙齿痛,她要给病人针灸,病人不敢,怕痛,她就先给自己扎。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100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 王桂珍的这种类似过去乡村游医一样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时也参加部分农业劳动的方式,并没有引起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卫生部门的重视,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学雷锋的范围来宣传。因此,王桂珍的事迹,当时仅局限于上海基层。 与王桂珍的事迹相联系的,还有另一个人——黄钰祥。黄钰祥,1953年苏州医专毕业。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妻子张蔼平相继被分配到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工作,直接为农民治病。他在工作中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农民看病难的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江镇公社卫生院的条件极差,就是一幢租的民房,没有高压蒸汽消毒设备,连高压锅都没有,针筒等最基本的医疗器械是用煮沸的方法消毒,而这都是不合格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黄钰祥仍然想尽各种办法为农民治病。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与了江镇公社培养当地乡村卫生员的工作,成了包括王桂珍在内的第一批农村医学速成培训班学员的老师。 王桂珍、黄钰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这个词就这样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 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上海川沙县和市卫生部门宣传王桂珍、黄钰祥的事迹已经近3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二人的事迹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了一些值得在更广范围推广的经验,上海市于是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并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写作中,记者们首次使用了当地农民对王、黄二人的称呼——“赤脚医生”,并直接将全国人民都生疏的词“赤脚医生”用到了标题上,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夏天,在全国有影响的上海《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北京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3个重头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当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阅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批示很快下达,并且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更重要的是,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5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么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农村大队合作医疗制度建立 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当时,他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医生。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摸底,借鉴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办供销合作社摆脱奸商剥削的经验,考虑到了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和疾病作斗争的思路,拿出了《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这个草案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肯定和支持。为了将覃祥官的草案变为现实,乐园公社大力支持杜家村大队办卫生室。 1966年8月10日,这个处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卫生室挂牌了。这个合作医疗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 同时,在覃祥官的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病。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中共湖北省委对覃祥官的事迹和杜家村大队的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宣传和推广。就在毛泽东作出“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不久,中共湖北省委于1968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4个字:“此件照办。”毛泽东的批示,是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肯定。 从此,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在大队一级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了。 据《湘潮》 |
||||||||||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默认
默认